
新闻热线:028-86696397 商务合作:028-86642864

新闻热线:028-86696397 商务合作:028-86642864
杨庆珍,网名“蒹葭”,头像有亮点,那西岭山腰的一朵小众细花。这画风让无数读者感动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“我是一棵芦苇,出生在白露。”“白露为霜,芦苇也白了,万物都有感应。”“光阴倏忽而逝,我也经历四五十个白露了。”作为一个同病的乡下“植物人”,躺平于城市生活,我在这样的文字前面,竟然还能安静和矜持,愿意一字一句复述,就像复述久违的身边人身边事一样。
一个看闲看淡、与世无争的“植物人”,沉浸于草木生活,聊叙婉约三五,记录怀柔点滴,这是我曾经向往而不得的语境,也是我对杨庆珍散文新著《山间四季皆滋味》《人间草木有深情》(2024年11月,成都时代出版社),面上的印象与内里的感动——我辗转反侧做不到的,杨庆珍不动声色地做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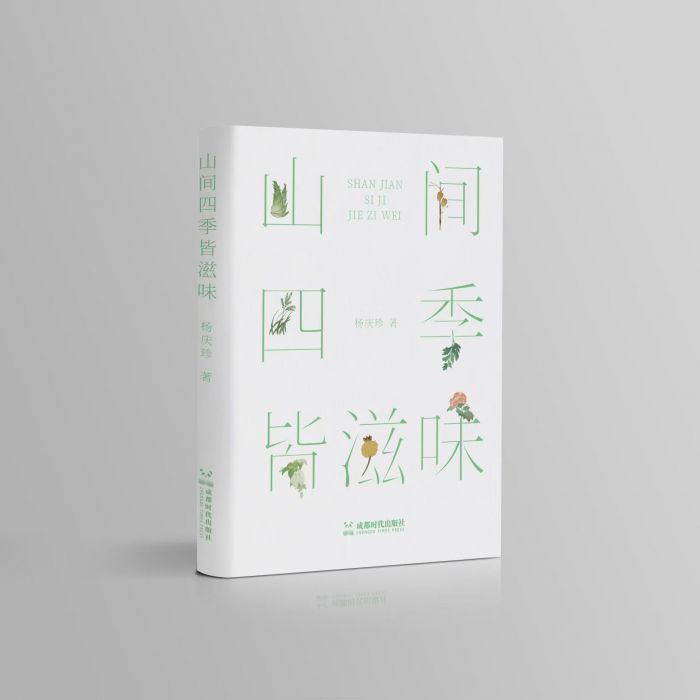
《山间四季皆滋味》
写植物,写成植物学或者名物文化,这是我们容易看到的常态。但把植物当“我”或“我”的影子倾述,俯下身子,让笔触倒影于斯,述着写着,恍恍惚惚,“我”和它们,揉在一起了,彼此分不清了,怦然心动了,呓语呢喃,芬芳四溅,这是杨庆珍的陌生、小众以及代入感,也是杨庆珍成都丘陵山区拟物生活的常态。曾经,我在陶渊明和性灵派那似曾相识,后来在汪曾祺和贾平凹笔下再见,今天我在杨庆珍这里,情不自禁地驻目下来,驻目于那草木的深情与四季真味。
枇杷茶,“这是陆游喝过的茶”,杨庆珍的研究心得。我记住它,因为另一个拟“我”的名字——“山中客”,“我”是此山此刻的主人,也是此山此刻的客,包括你,“我”,还有放翁,我们都被一种叫枇杷茶的草木主宰。这大约是我读到过最为复杂的托物寄寓。四位一体的治愈啊!
艾是治愈的。仁慈的艾,“浓厚饱满的气息,那么深,带着药味”,它治愈了“喝完这碗药的人”,也包括“我”。石斛先生也是治愈的。先生是一丛石斛,“状如竹叶,坚硬厚实”,先生也是卖石斛的隐世老人,“形貌清癯”。石斛与先生的附身,就像“神与物融为一体”,两两治愈了“我”,“让人在呼吸之间感受到真正的清凉和安稳”。同样治愈的还有厚朴、黄柏、杜仲、黄连、白芨、重楼……如数家珍呀!杨庆珍并未止于多味药香的治愈,葱茏生发中,竟然听到草木的灵魂神曲,“一声叮当、叮叮当,时紧时慢,时高时低,悠扬婉转……”是什么引发作者感觉的时空大挪移?陆放翁的绝句?大诗人的七言即兴,只是环境的偶然勾连。而“捣药鸟”的鸟鸣不止,才是那些治愈草木的永恒的有声倒影。而“我”,是此情此景的总成,“人在山中,肉身也几乎消弭无影。只有捣药鸟化作的无数药材,与山林溪涧同在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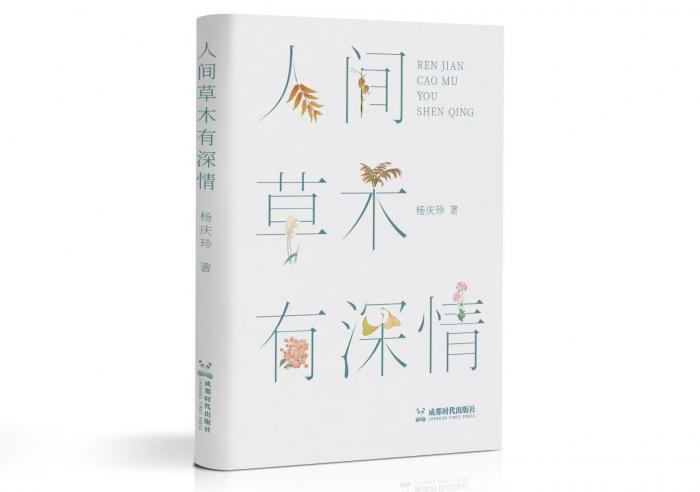
《人间草木有深情》
杨庆珍植物抒写的核心价值,就是“我”,或物我不分。她不需要刻意拘泥于植物常识或文化史陈的丝丝入扣。很多非虚构作家热衷于这样的跨界求证,求证的同时,也消弭了“我”——汉语小品文本身的魅力。
杨庆珍的草木抒写,更像在搭建一个童话般的“女人花梦”。女人花是安仁古镇的老柚子树,“年轻得很,每年开花繁盛,结果累累。”“它们是老品种的柚子,如今只负责审美。”确定作者这是在说柚子?而我看到的是,“上个世纪月份牌上旗袍女人还站在墙上”“暗地妖娆”,民国迟暮美人的梦,原来让古镇上一群着旗袍的女人给复活了。她们之中,有一个注定是“我”,“在柚子树下想得太多,似乎小睡过去,做了一个悠长旧梦。”女人花是蔷薇,小区广场上跳舞的她,“身材略有些臃肿”“且舞且蹈,自由自在”。女人花是乡村的晚饭花,像乡下熟悉的女子,比如“我”的舅妈和母亲,朴实强健,勤俭持家,生儿育女,“倾尽全力地活着”。女人花是母亲的皂荚树和棉花草馍馍,母亲用皂荚为“我”洗出一头的植物清香,给“我”做干净好吃的棉花草青团。多年后,它们总让“我”想起她们,“从青草的芳香中回味童年的味道”,终将成为“我”一辈子凝望的方向……
更多的时候,杨庆珍是在写自己——总要回到自己。回到自己,就是回到自觉,回到叙述和抒情的本来——原来“我”就是那个最持久、最芬芳的女人花梦。“我”从“蒹葭”开始,就把自己等同于一棵草木了。没完没了的草木芬芳,没完没了的女人花梦,没完没了的“我”以及乔木杂树山花小草的自言自语……“我”是桃花么?“飘零于时间的水上”,那为何早习惯了打坐,“在宏阔的时空中等你”?“我”是栀子么?“花瓣逐渐萎黄”,那为何“幽香一旋一扭地,似有若无,似去还留”?“我”是睡莲么?“有点懒洋洋的味道,似乎在做梦”,那为何“一抿嘴,酒窝就荡漾出来了,一圈圈涟漪就扩散开去”,那么清晰?“我”是红蓼么?“萧疏清远”,“无人问津”,“田野是我的宿命”,那为何又“开成了海洋,开成了火焰”,“内心,汪着一潭秋水”……难道,“我”是薄荷,“有人闻起觉得冲鼻刺激,有人觉得很爽,提神醒脑”,“我”是紫苏,“灵魂有香气的女子”,暗自朝向自己发“一层柔情缱绻的香”……
合上两本清香四溢的美文,我陷入了一种暗香的渊薮,我是被杨庆珍乡间文字的旖旎气质打败的,我更是被那草木的光影升华和照见的……
这就是杨庆珍,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意识和自觉意识的写作者——把花草树木视作肉身肌肤感官契合部分的女子,把缓慢的文字无缝镶嵌进日常审美,并试图延长有限写作生命于无限审美可能的女子……
汪曾祺写植物,每一个文字的追根溯源考证,只为寻找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,表达对于万物的爱与关怀。同样归属于简朴的草木抒情一类,杨庆珍与汪曾祺不一样的是,普世的爱和关怀,首先也是终将指向“我”自己的。
唯有嗟叹……
我曾经问过杨庆珍,为啥把观照的目光和情感,毫不吝啬地投射于“不招人待见”的山野植物?我这么问,试图也给自己找一个参照,因为我也曾不厌其烦地为它们倾尽过辞藻和修辞的才华。她荡开问题本身,微信回复我一个似是而非的说辞:“喜欢这样的精神自由,自在旷达。”这话,有些“官方”,我是同意的。我是杨庆珍的真实读者,更是她笔下草木的柔软同类。我们所以抒写,因为表达对于日常共鸣的态度或者信仰。
 相关推荐
相关推荐